文藝 孫先科:一個歷史“跨界者”的形象“代言” ——王蒙“自傳性小說”中的自傳形
原標題:文藝 孫先科:一個歷史“跨界者”的形象“代言” ——王蒙“自傳性小說”中的自傳形象與“代際”書寫
王蒙小說創作中有一類作品塑造了一個與作家本人或親人、朋友對位性很強的人物形象系列,《王蒙自傳》的出版印證了這類作品的“傳記性”但王蒙對其小說的“傳記”命名。“自傳性小說”的命名既指出王蒙此類小說的“傳記性”又指出與“自傳體小說”的區別,即以復數“我們”和“代際”為主體的自傳性書寫。王蒙是一個者,但他進入的時機和作為“外圍”的經歷決定了他“亞主體”的歷史地位。王蒙書寫的主體就是新主義的“亞主體”——“青年近衛軍”在當代歷史中的歷史際遇與心靈史。在創作的初期,王蒙就與眾不同地寫出了在混沌的生活面前試圖睜開眼睛,思考著找尋生活意義的年輕人,寫出了他們面對“引人”的成年世界和“真正的生活”的焦慮與惶惑。20世紀80年代重新回歸文壇,作為“早早‘首先’入了黨”的王蒙,其自傳性形象是通過對“黨的兒子”的身份確認和對詩人身份的反思來進行主體性的重新建構。“季節系列”是對以前作品的一次規模宏大的“重寫”,也是“自傳性小說”在品質上的跨越。
本文原刊于《文學評論》2018年第2期,感謝作者孫先科授權文藝發表!

閱讀王蒙的一部分小說,如《青春》《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布禮》《活動變人形》等,常常會產生一種自傳性聯想。“四季”系列長篇小說的發表,錢文的人生徑與王蒙的“故國八千里,風云三十年”高度吻合則更加強化了這種“自傳性”的認知導向。將王蒙的生活世界和他的文學想象世界作為“互文”看待,從“傳記”或“自傳”角度閱讀、闡釋他的文學創作是否可能?有何價值?

《王蒙自傳》三部曲(《半生多事》《大塊文章》《九命七羊》)分別于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出版。在“自傳三部曲”中,作者立體、全方位地描繪出自己豐富多彩的一生,尤其是《半生多事》對自己家族史的追述,對童年、少年時期的閱讀、觀影、聽聞及夢想的描摹,對初戀和婚姻的閃爍其辭又真摯多情的回憶,對如何邁人門檻、與其他者結成的友誼、成功后的歡欣鼓舞的深情再現,對初人文壇的緊張、興奮、尷尬的呈現與辨析等,讓我們為他的小說創作找到了一個發生學的淵源和基礎,為林震、趙慧文、鄭波、倪藻、倪萍、鐘亦成、周克、翁式含、錢文等諸多人物找到了闡釋學上的依據,為從文史互證角度展開的“傳記式”找到了性的根據。

但王蒙明確表示“我的作品除寫新疆的《在伊犁》外,從來沒有什么原型,卻有生活中某個人物某個事件的。寫出來以后,人物都是王蒙的創造與想象,他或她已經與了王蒙的那個人脫離了關系。脫離了關系卻又引起了回想。”①王蒙對他的小說人物與作者或生活原型“若即若離”關系的描述似乎與魯迅先生對文學人物創造時“嘴在浙江,臉在,衣服在山西”②的說法有著類似的美學旨趣,因此,將他的小說或部分小說命名為確切意義上的“自傳體小說”或“自敘傳小說”無疑存在著理論上與實際上的困難,盡管我們在他的小說中經常地、確切無疑地能夠指認出某些人物形象與生活原型的密切關聯(如倪吾誠與作者父親的關系、錢文與作者本人的關系,等等)。
盡管如此,我仍然嘗試將王蒙的一部分作品稱之為“自傳性小說”,從作者與他小說世界相關聯的角度來考量、闡釋他的文學創作。王蒙特識獨見的思想方法中有至關重要的一條:任何事物都要承認有“中間地帶”③,涇渭分明、非黑即白的思維與判斷是有害的。“自傳性小說”這種策略性的命名可以實現對某種“中間地帶”的描摹與。具體而言,這一命名的內涵與理據可概括為:第一,王蒙巨量的小說創作中有一個以作者的經驗為基礎,主人公的思想、性格與作者有著高度相似性與一致性,在作者不同階段的創作中反復書寫的小說系列,如20世紀50年代的《青春》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80年代的《布禮》《如歌的行板》《雜色》《相見時難》和《活動變人形》,90年代的“季節系列”與《青狐》等。雖然確切的“自傳”指稱有些勉強,但是,從整體上來看,這一系列小說塑造出一個相互關聯的、自洽的人物形象系列。就其主體性而言,作者本人與這一人物系列有高度的自指性和認同性。第二,王蒙反復表示要為一去不返的時代留影,為時代、為一代人樹碑立傳的寫作意識強化了這一系列作品的傳記性。第三,王蒙本人的經歷極其復雜,介人時代與社會極深,他本人就是勃蘭兌斯所說的“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④的人,從“自傳性”視角切入的研究無疑會強化他的小說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互文”關系,更強烈、更深入地出他小說創作的思想史內涵。第四,從文體學的角度來說,他的這一系列小說,尤其是在“季節系列”中,作者有意使用“我一你”這一稱述結構,形成第一人稱敘述者向在場的受述人講說故事的敘述模式,而且作者以“老王”的身份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種類似《史記》的“史傳體”體例,為“傳記式”閱讀提供了內部的文體學支撐。

當然,采用“自傳性小說”這一命名方式也是為了與“自傳體小說”這一嚴格的稱謂進行區分。區分的依據除了傳記形象與傳主經驗的相似度以及“作者一敘述人一人物的三位一體”這一自傳契約外⑤,我更看重的是王蒙這一書寫方式在根本“氣質”上與“自傳體小說”的不同:一是傳主的復數化,“我們”是主語,“代”的意識、對話的意識大于個人意識。二是“我們”的成長指向思想的“成長”——成長這一美學概念甚至都不能完全描述“我們”的狀態與變化軌跡,因為“我們”不僅表現為線性的、邏輯化的性格梯次發展,而且表現為“群”“代”之間的對話、爭吵和“自反式”的質疑、探詢,表現為人物心態和思想空間的無限擴展。如果說用“成長”或“成長小說”的模式闡釋“自傳體小說”經常是有效的話,用“自傳性小說”和相應的范疇應對的不僅是王蒙對人物性格的塑造,而且是一種彌散式的心靈空間的營造與“思想史”的書寫。
王蒙出生于北平的一個知識家庭,父親曾留學,受到過文明皮毛式的熏染,不諳、懶理功業的性格特點既導致事業的失敗,也導致家庭的貧困和家庭關系的失和。王蒙后天一再的“平民”出身應該來自一種切膚的感受。平民出身和每況愈下的生活處境,加生的、早慧,使王蒙自然地“唯物主”了道。
王蒙是一個者、一個早熟的進步青年,但時期的王蒙是的外圍⑥,北平的和平解放使他成為不戰而勝的勝利者,這使他與真正的者之間隔著一層似有若無的屏障。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和歷史主體,王蒙是一個員和者,但與那些真正參與新主義的者相比,王蒙的者身份顯然缺少了一些槍林彈雨和出生入死的背景,在倫理關系和形象的想象序列中退居到次一級的上。王蒙和他稱之為“我們”的那一代人的身份用“青年近衛軍”⑦或許能得到更準確的描述。
從另一方面來說,王蒙的“平民”出身又是可疑的、不切實際的。童年時期,在父親的影響下,王蒙就有了豐富的看戲、觀影、讀書、賞樂的經歷。這種并不“平民化”的培植和養育過程,顯然既給了他最初的藝術養分和審美訓練,也為他后天成為一名好學深思、愛追問、愛分析的作家鋪就了土壤。王德威將“抒情”這一傳統上的表達手法和文類概念上升為“一組政教論述,知識方法,感官符號、情境的編碼形式”⑧,王蒙就是帶有這種“抒情”特征的天生的詩人。也就是說,就其作為一個主體的結構性特征而言,王蒙具有一種典型的“中間人”特性,不是“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的“零余者”,而是一個“多出一厘米”的“跨界者”⑨。
從歷史性的維度而言,王蒙和他稱之為“我們”的一代人是新主義的后來者、晚生的“青年近衛軍”;從結構性的維度而言,王蒙又具有者/詩人、中堅意識/邊緣感的跨主體的雙重特性。這種歷史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的獨特結合構成了王蒙作為一個歷史主體的特殊性與復雜性,這也決定了王蒙的“自傳性形象”成為獨特的“這一個”以歷史主體自命但又徘徊猶疑;神圣的擔當意識、主人公感和自審、意識相糾纏;上下求索、左顧右盼既是他的思想方式,也塑就了他的命運軌跡。與“歷史小說”所塑造的那些者與先行者如江華、盧嘉川、江姐、許云峰等相比,他們既沒有先輩們的歷史,也缺乏先輩們堅定不移的思想和鋼鐵般的意志。同時,也不同于林道靜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宿命般地成為一個在中學習、在學習中的“者”。“青年近衛軍”作為特殊歷史主體的獨特性就體現在他的“跨代”和“跨主體”的中間性特征。
《青春》和《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王蒙在20世紀50年代的兩部代表作,是他“自傳性小說”的最早作品。細讀可以知道,兩部小說的主人公鄭波和林震正是對社會和歷史高度但似乎又處于某種邊緣狀態的“動態”人物,兩人的名字“波”與“震”提示的也正是這種“動”的特質。在思想和行為上的“左顧右盼”“上下求索”構成了他們的基本存在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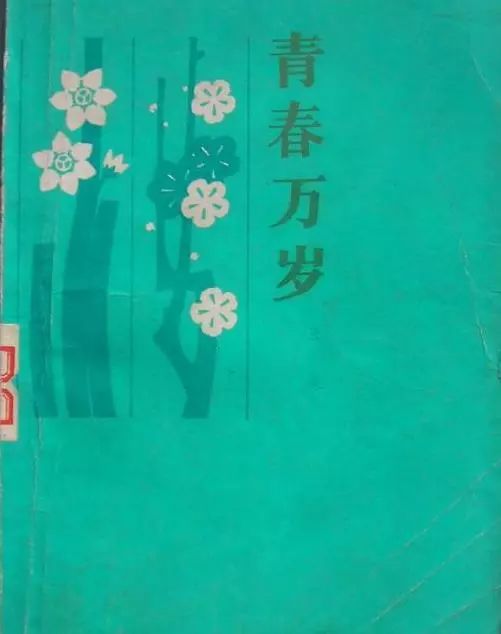
鄭波是一個年輕的“老”,在女中這群活潑可愛的女孩子中有著早熟的經歷,在一派天真爛漫的女生中顯出獨特的憂郁性格。她的憂郁來自她的,來自她對人生和愛情選擇的左右支絀,歸根結底來自于她身份的“中間人”特征,即“跨代”和“跨主體”帶來的人生選擇上的波動狀態。她是中學生中少有的,經歷人人羨慕,但她卻為自己的學習成績不好而苦惱,因為她地意識到在一個“大建設”的年代只紅不專是不合格的人,在袁新枝、李春等更年輕、學習成績更好的同學面前,她常常感到自卑。田林的愛慕與追求讓她體驗到了愛情的甜蜜,但她又時時感到恐慌,她田林的追求并最終了他。她田林的求愛看似奇怪,實則有更內在的邏輯在支撐。一方面,在她的內心深處男女之愛是一種成年經驗,與她的學生身份不相稱,面對更年輕的一代時,這種經驗讓她覺得羞恥。另一方面,她窺視、猜度著引人黃麗程的世界,黃麗程婚后沒有血色的臉、燙過的卷發等暗示了婚姻生活的性,這種的氣息讓她望而卻步。在一部以塑造群像為旨的小說里,鄭波的經歷和內心世界還僅僅是被掀開了一角,我們已不難發現這是一個典型的“夾在當間兒”的、在兩代和兩個歷史主體之間觀望徘徊、尋求歸屬的人物⑩,與作者有強烈的相似性,是作者指涉性很強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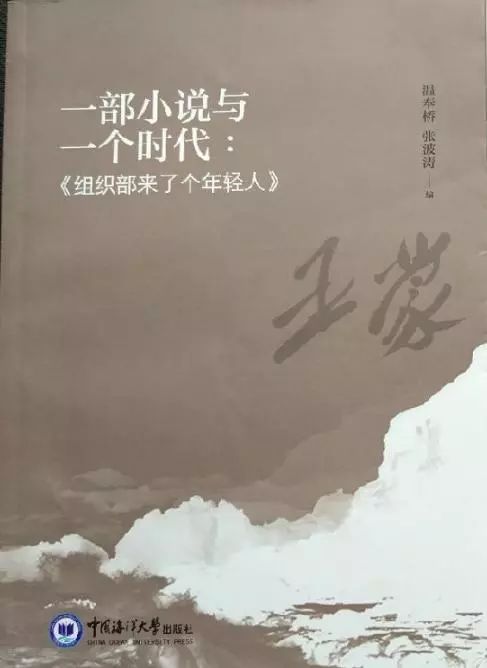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在很長時間里被作為一部“反官僚主義”的作品來閱讀和闡釋。依據這一定位和已經習以為常的闡釋邏輯,林震被視作與劉世吾和韓常新相對立的“反官僚主義”者、一個的英雄人物就是必然的了。正是從這一闡釋思出發,有人認為“正面人物寫得不好”⑪。王蒙自己說“我并沒有試圖把林震當英雄典范來寫”⑫。在我看來,林震和鄭波一樣是一個處于觀望和思想波動狀態的年輕人,作者構思的核心是將他作為一個“準主體”“亞主體”來寫他面對社會和歷史的中心(組織部是社會運轉的核心機制的隱喻)、那些處于社會機制中心的過來人、先于自己進入成年世界的志同道合者時,內心產生的變化與震蕩。因此,林震不是一個二元對立模式中的一極,劉世吾不是他的敵人(同時還是他的“兄長”),趙慧文也不完全是他的同道(趙慧文荒蕪的屋內陳設和她不如意的婚姻引起他對成年世界的,這時趙慧文是他審視的客體),他是混沌的生活狀態中的行人,他摸索著、思考著、成長著。
這或許就是王蒙的與眾不同和出類拔萃,在一個英雄和他們的敵人構成的簡單明了的文學世界里,王蒙寫出了在混沌的生活面前試圖睜開眼睛,試探著、思考著找尋生活意義的年輕人。年輕人的突出特色不是表現在他的通體透明似的崇高,而是表現在他們思考生活的嚴肅、認真,表現在他們作為一個特殊的歷史主體在新生活面前的惶惑與思考,表現在和大多數“新人”的單質性與化不同,一開始就體現出在代際之間、不同歷史主體之間對話、質疑的思想者氣質。這是王蒙的文學起點,某種意義上也是年輕的王蒙自己思考和尋找生活意義的起點。王蒙和他筆下人物在思想歷程上的同步性是他小說“自傳性”的基礎和特色。
正是由于“跨代”、尤其是由于在結構上“跨界”的主體性身份——具體而言,作為詩人的“抒情”特征,好思考、好分析、好質疑的異見性眼光與聲音讓王蒙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的運動中被拋出了生活的核心地帶,游走于社會生活的邊際角落。“故國八千里,風云三十年”是他這段生活的真實寫照。但從中心的游離,使王蒙有機會深入到更廣闊、更粗糲、更本真的生活中去,在深刻認識人民大眾的同時,對也有了更深入的反思與認知。《布禮》《如歌的行板》《相見時難》《蝴蝶》《雜色》《春之聲》《夜的眼》《活動變人形》等作品正是這段生活和思想軌跡的真實記錄,鐘亦成、周克、翁式含、倪藻等人物形象則是他進行歷史反思的具象化載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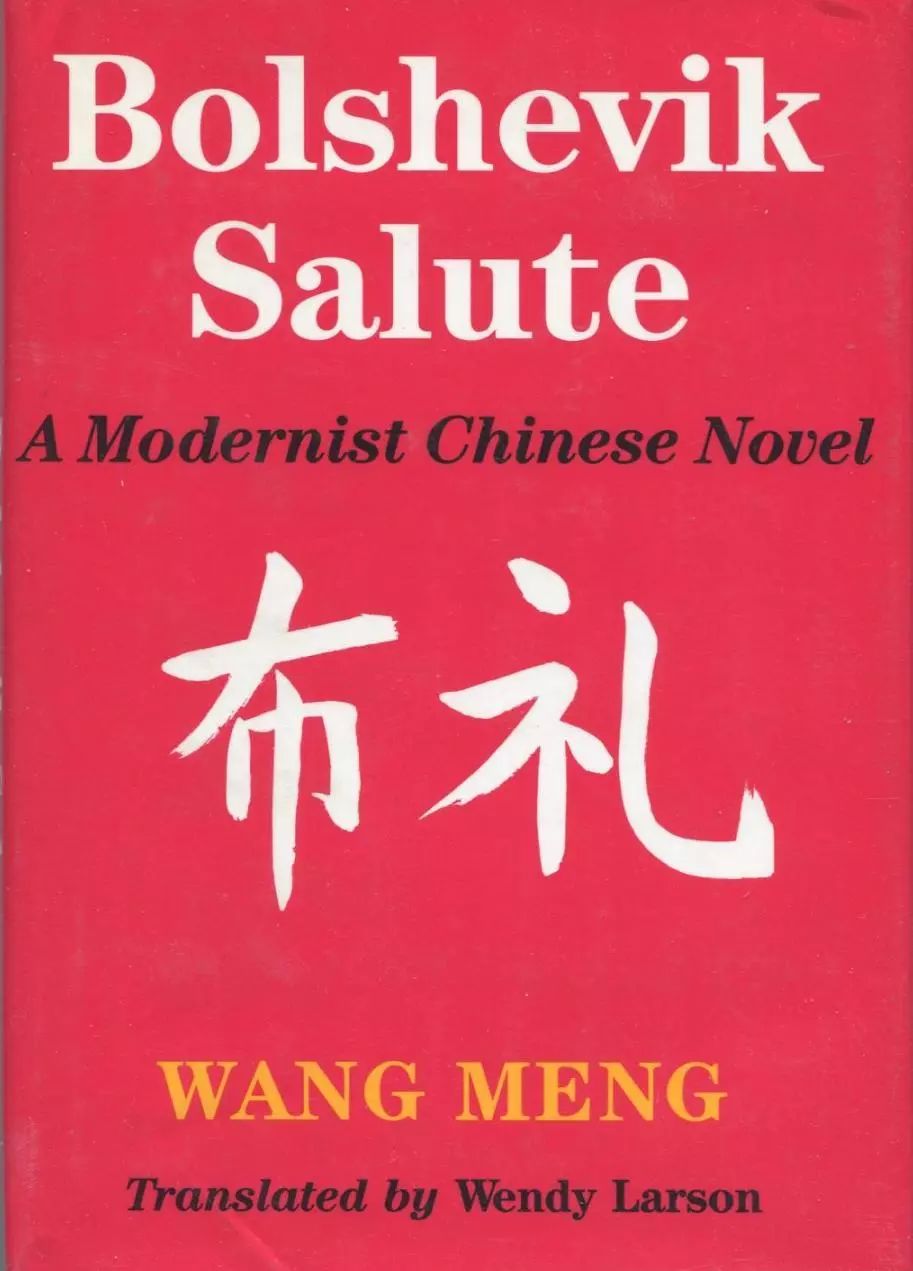
王蒙自稱是“夾在當間兒的”,自稱“我早早地‘首先’入了黨,后來才嘗試創作。我無法淡化掉我的社會身份和社會義務”⑬。那么,“‘首先’入了黨”的王蒙和他的自傳性主人公在回歸的過程中“首先”面臨的主體性問題是:我是誰?我曾經是一名神圣的員……一個特殊的時代結束了,我究竟何以自處?那個“無法淡化掉的社會身份和社會義務”仍然是有效的嗎?或者說,什么才是我在新時期的“社會身份”和“社會義務”?
首先,“黨的兒子”的身份確認與主體性的重新建構。《布禮》是王蒙復出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說,主人公鐘亦成是一個早熟的者,年紀輕輕即黨的核心部門的領導崗位。1957年,他因一首小詩而被地,他委屈、不解:“你怎么不問問我是什么人呢?怎么不了解了解我的歷史和現實表現,就把我說成這個樣子呢?”鐘亦成的潛臺詞是:我是黨的人,怎能將一個歷史和現實都忠誠的說成對黨和黨的事業心懷呢!1957年鐘亦成正式被宣布為黨的敵人,這種上的否定帶給鐘亦成的震撼類似于一場外科手術“鐘亦成和黨,本來是血管連著血管、神經連著神經、骨連著骨、肉連著肉的……鐘亦成本來就是黨身上的一塊肉。”宣布他為黨的敵人等于將他從黨的肌體上割除、拋掉。“對于鐘亦成本人,這則是一次胸外科手術,因為黨、、主義,這便是他鮮紅的心。現在,人們正在用黨的名義來剜掉他的這顆心。”或者說,這是一個比死刑判決還要的宣判。
于是,鐘亦成開始了他的雙重“流浪”:工作生活上的放逐以及上的左沖右突和上下求索。時空交錯、人與、與他者變成了鐘亦成存在的現象學事實,年輕的者這一歷史主體零散化為碎片化的人。經歷了對自己紅色根性的反顧與確認,經歷了對自己單純、幼稚、過分浪漫和耽于想象的反思,經歷了對幽暗人性的洞察,經歷了在勞動中與人民的接觸,那個被肢解和零散化的鐘亦成才終于宣布了自己重新歸來。這時歸來的鐘亦成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鐘亦成,而是一個經過了否定之否定之后的“新人”,一個新的歷史主體“當我們再次理直氣壯地向黨的戰士致以布爾什維克的戰斗的的時候,我們已經不是孩子了,我們已經深沉得多、老練得多了,我們懂得了憂患和,我們更懂得了戰勝這種憂患和的喜悅和價值。”
《布禮》被有些人認為是王蒙向黨表達的忠心。這沒有什么錯。就像鐘亦成因詩獲罪,被懷疑對黨不忠時的反應——“你怎么不問問我是什么人呢?怎么不了解了解我的歷史和現實表現,就把我說成這個樣子呢?”——一樣,王蒙首先是一名,黨的忠誠的兒子這一身份是他的“前世”,也是他的“”。當經歷了的放逐之后,重獲這一身份就是他宣布回歸的重要標志。

其次,對“抒情”詩人身份的自反式的審視與剖析。所謂“抒情”特質,落實在20世紀50年代的王蒙身上,就是在一個要求步調一致、思想統一、集體倫理統攝一切的與文化語境中如何表達個人獨特的感受、思考和意愿。像鐘亦成用詩歌表達自己的困惑和感受,像周克對《如歌的行板》的與鐘愛等,這些“抒情”的獨特氣質和身份顯然與身份和思想高度的一體化是異質的、甚至是悖離的。對這種詩人與生俱來的“抒情”特質的反思構成了王蒙80年代初期自傳性形象塑造的一大特色。就是說,王蒙在新時期的回歸和他創造的“回歸者”一方面以“黨的兒子”自認,另一方面對自己的“抒情”氣質和詩人身份進行自剖和。如在《如歌的行板》中,周克等人對柴可夫斯基這首名曲的旋律是如此,對這曲子所內涵的溫柔、美好的情愫神魂。他們因偷偷地欣賞此曲而罹難、而被放逐。經歷了后回歸的、成熟的周克“超越”了、否定了以前的自己:面對真正的、的、波瀾壯闊的生活,《如歌的行板》的溫柔、纏綿、美好就顯得過分柔細過分脆弱了。
再次,經歷了多次運動的大浪淘沙,被王蒙稱為“我們”的一代人作為一個統一的歷史主體出現了離散的蹤跡,這一共同體中既有像王蒙這樣重拾、重建主體性的“黨的兒子”,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主動或被動“出局”的人,這些“局外人”在此時的小說中以“他者”的存在方式構成了對王蒙“自傳形象”的反觀和補充。一是頹廢的、看破的混世者,如《布禮》中的“黑影子”。二是了祖國與的畸零者,如《如歌的行板》的金克和《相見時難》中的藍如玉。在塑造這類形象時,王蒙使用了一種共同的修辭,即一種美學的分身術,如《布禮》中的黑影子實際上是鐘亦成一體兩面的對話者;《如歌的行板》中的小克、大克、老克實際上就是一個“克”,即“布爾什維克”,三人的不同人生道,代表了王蒙對“代”的思考、對“我們”作為共同體的思考出現了“分化”的苗頭,三個“克”指稱的是“我們”中不同在時代的大浪淘沙中的不同人生選擇。
不論“黑影子”還是混世者、畸零者,他們都是作為王蒙自傳形象的“他者”而存在的,他們的在場反證了“黨的兒子”重拾的與可貴。這種一身幾個影子的修辭策略也說明,在王蒙的認知視野中,“我們”的確是作為一個共同體存在的,但這一共同體開始出現了裂解的征兆,預示著在將來的創作中,‘我們”只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隨著每個個體被賦予主體性,“我們”將成正復數化的主體群像。
20世紀90年代,王蒙開始“季節系列”的寫作。這部氣勢非凡的“長河小說”與王蒙此前的小說存在明顯的“互文”關系,是他的“自傳性小說”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作品。所謂“互文性”主要表現在:一是以自傳形象為中心的人物關系結構和“放逐————回歸”的人生模式依然是“四季”話語體系的骨架;二是就小說講述的經驗性質與經驗類型而言,“四季”與此前的自傳系列有高度的同質同構的性質。“四季”可以被視作對此前自傳書寫的一次大規模、深層次的“重寫”,是王蒙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對自己人生經驗的一次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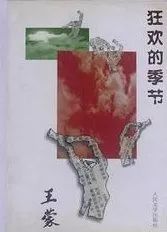
“四季”寫作的20世紀末、21世紀初,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王蒙“想要說出”和要為一代人樹碑立傳的愿望不僅有了可能實現的,而且由于、文化語境的深刻變革,使王蒙對自己和他同代人的思考獲得了巨大的空間。因此,“四季”的“重寫”不是重復,而是一次新的跨越。突出表現為兩點:一是錢文作為一個與作者對位的自傳性形象比以往的任何一個自傳性形象都得到了加強;二是其他人物也獲得了充分的主體地位,形成了“一世——三代——(甚至包括了貓和雞)”的形象系列,復數“我們”而不是單數“我”的傳記化才真正實現了作者為“一代人”樹碑立傳的愿望。
在所有自傳性形象中,錢文是與作者對位性最明顯、傳記性最強、思想含量最豐富的一個。首先是傳記經驗的完整性。鄭波、林震、鐘亦成作為自傳性形象,只涉及作者人生傳記經驗的局部,截取的是作者傳記經驗的片段與截面,是作者人生鏡像的某一點或者某一個側面,其中家族與童年經驗的缺席使這些自傳性形象與作者豐富完整的人生經歷相比具有結構性的缺陷,其審美和歷史認知的深度與強度被嚴重局限。錢文的出現,家族和童年經驗、新疆經驗的出場才使王蒙的自傳性形象真正完整、豐滿起來。惟其如此,王蒙試圖通過自傳性書寫來達成對“一代人”進行真實記錄和描繪的意圖和目標,才找到了美學的支撐和的形象基礎。
錢文不僅在生命的長度和經驗的寬度上超越了他的“前任”,更重要的是錢文在跨越了“故國八千里,風云三十年”的滄桑歲月,經歷了從戀愛、失態、躊躇和狂歡的“四季”的淬煉之后從性格與思想層面上完成了自己的成熟化與成年化。50年代“戀愛的季節”時的錢文是一個將“現實/理想”“/集體”“階級/人性”對立起來,性格明亮但認知簡單的年輕人。在經歷了“失態的季節” “躊躇的季節”和“狂歡的季節”之后,錢文成熟了:他認清了更多的現實但仍不失熱情與理想,“青年近衛軍”的血液仍在血管里奔突;他懂得了個人和人性的重要性,但仍以自己是一名員而自豪;看到了歷史的扭曲甚至倒退,但仍對國家民族的未來充滿信心。小說盡管沒有給出錢文一個終極的、定于一尊的性格和思想終點——他的性格與思想仍然是敞開的,但無論是對個人、對社會、對歷史、對現實、對、對、對國家、對民族的認知無疑具有了具體而充盈的內容,與50年代的錢文相比,中老年的錢文顯然變得更寬容、更駁雜、更睿智。從年輕時的簡單明亮到中老年的寬容、駁雜、睿智,這就是錢文的人生,這也是王蒙完整的人生鏡像。錢文形象的成功塑造使王蒙筆下的自傳性形象系列有了一個收束,有了一次總結,王蒙念茲在茲為一代人樹碑立傳的愿望有了一個一以貫之的綱領。
還不止如此。“四季”巨大的思想含量與美學價值還表現在錢文作為一個歷史洞察者在建構自己作為一個歷史主體的過程中,在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中識別出自己,也識別出“他者”。這一洞察與識別過程提供的是錢文/王蒙真正的自傳、心靈自傳,是分析學層面上的成長與成熟,與社會歷史層面上的成長與成熟互為。
有兩個層次。第一,是通過對“我們”、對“青年近衛軍”作為統一的歷史主體的消解和否決完成的。在泥沙俱下的歷史潮流中錢文逐漸發現,在他稱為“我們”、連上廁所也要共同行動的者集體并不是鐵板一塊,并不具有永遠的統一意志、統一的屬性,一句話,“我們”無法作為一個單數的歷史主體面對歷史的肆意沖刷。趙林是“青年近衛軍”團隊中的之一,對上級篤信不二,總是地、激昂地同伴,但在經歷了命運的一波三折之后變成了一個意志消沉、看破的市儈。李意作為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兒子千方百計地自己爭取“不掉隊”,爭取和大家一個樣,但終究還是和大家不一樣,不得不作一個“逍遙派”。祝正洪出生在城市貧民家庭,看起來誠實、憨厚、樸訥,但他是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他是天生的藏鋒守拙、韜光養晦的大師。得益于此,他幾乎是“青年近衛軍”中唯一一個在事業上一帆風順、官運亨通的人。這個看似厚道的人為保全自己不惜偽造事實,向自己的發起致命一擊,顯示出他陰辣的一面。祝正洪身上顯示出中國文化性格的諸多隱性密碼,是單純明亮的現代文化不可能孕育產生的,在王蒙以前塑造過的“青年近衛軍”這一形象陣營中從未出現過如此復雜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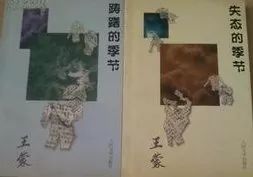
“季節系列”和《青春》相似,是結構宏大的群像小說。“一代人”的群體形象是作者書寫的重心。但通過比較會發現《青春》中的中學生群體存在不同性格,但并不存在不同的“語言形象”和“語言主體”⑭,而“季節系列”中的幾個主要形象突破的不僅是性格,如李意和祝正洪,而是突人了另外一種語言體系,是說出了另外一種語言的“語言主體”和文化主體。“季節系列”不僅是規制宏大的“長河小說”,而且是真正意義上的“復調小說”,它告知我們在被認為有著共同和屬性的“一代人”中其實存在著不同的分野,在歷史的沖刷之下,一個鐵板一塊的共同體是不存在的。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的消失,意識到“一代人”實際上是由各種各樣的歷史個體共同組成的,標志著錢文真正的成熟,標志著他作為一個歷史主體的自覺。
第二,是在不同的代際之間發現了“我”和“我們”的性,在與“介體”與“助體”的對比中發現了“代”與“代”、“性別”與“性別”之間的差異性,發現了他們各自作為歷史主體的主體性。在王蒙“季節系列”以前的“自傳性小說”中,存在著一個以自傳性形象為中心、為主體,以一個先行者、引領者和大哥身份出現的者為“介體”,以一個異性同行者為“助體”的想象性“三角關系”模式⑮。典型的如《青春》中以鄭波為中心,以黃麗程為“介體”、田林為“助體”的“三角關系”;《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以林震為主體,以劉世吾為“介體”、趙慧文為“助體”的“三角關系”;在《布禮》中以鐘亦成為主體,以老魏為“介體”、田雪為“助體”的“三角關系”,等等。這一“三角關系”的典型特征是,自傳性形象的主體性成長依賴于對“助體”和“介體”的觀察、審視、猜測、想象,在與二者潛在的和心靈的“對話”關系中確定自己的歷史地位和。這一“三角關系”最大的美學和思想史價值在于讓我們真正從心靈史的角度、從分析學的層面上看到了像王蒙這樣的“青年近衛軍”身份的歷史“亞主體”的成長過程,在主體化過程中復雜而又鮮活的心靈狀態。
但是,這一“三角關系”在美學和思想史上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即“介體”和“助體”某種程度上的符號化、隱喻化從而遮蔽、隱匿了他們作實的歷史主體的歷史行跡和豐富復雜的心靈世界。劉世吾、黃麗程和老魏,田林、趙慧文和田雪均因為在文本中被作為主體(敘事的內視角)的透視和猜度對象,他們的生活世界和心靈世界變得神秘而陌生。很大程度上他們是作為媒介和助手來促成、助推主人公在心靈上的成長和主體化的過程,而他們本身并未被充分主體化。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鄭波、林震和鐘亦成因為劉世吾和趙慧文等并未充分的寫實化、客觀化、歷史化、主體化,自己某些程度上成為“想象的主體”而不是“間性主體”。主體的“間性化”一定程度上是在“季節系列”中完成的。突出地表現為“介體”和“助體”由神秘化、象征化、符號化到寫實化,經歷了歷史的“祛魅”還原,直至成為一個真實的歷史主體。
“介體”:犁原和張銀波是文藝界舉足輕重呼風喚雨的兩個人物,他們在錢文進人文壇和成長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非常類似于老魏與鐘亦成、黃麗程與鄭波的關系,錢文對他們也有種亦父亦兄的親切感以及在上追逐和模仿他們的跡象。但重大的不同是,通過將他們充分地還原到生活情境中、完全地歷史化,他們作為偶像的歷史地位一點點的崩塌了。他們在上表現出的軟弱和騎墻行為消解了他們作為一個主體的神圣,他們在態度上的噤若寒蟬、唯唯諾諾在錢文眼里毋寧說是“猥瑣”的,與鐘亦成眼中老魏作為引領者的高大神圣形成強烈反差。張銀波在女兒身陷時表現出的絕情,在小錢文登門看望時表現出的冷漠和拒人千里之外的態度,以及犁原在與廖瓊瓊的愛情關系上的變節與行為幾乎可稱為不仁不義。俠肝義膽、情同手足的倫理關系了,引領者作為模本的偶像地位不復存在。錢文對犁原和張銀波的歷史化的敘述完成的是對一個歷史主體的和“祛魅”。當然這一“祛魅”的歷史過程在分析學和美學上的意義是雙重的:作為引領者的神圣和偶像地位被打破,一個更有和具體性(與卑下、堅定與軟弱等品性紛然雜陳)、更復雜多樣、更具立體感的歷史主體被重新建構起來;而作為者和模仿者的“青年近衛軍”也逐漸擺脫了作為歷史“亞主體”“次主體”的焦慮,結束了一直處于“波”與“震”中的心理狀態,從而獲得了作為一個的歷史主體的意識自覺和歷史自信。
“助體”:在“季節系列”以前的“自傳性小說”中,“助體”角色如田林、趙慧文、田雪在文本中的經常是處于被主人公觀察、透視、揣測的客體地位,沒有被作者的敘述觸覺直接觸摸,與主人公的真實關系基本處在一種想象性的支持者的地位,作為性別和歷史主體存在著不少盲區。在“季節系列”中,主人公錢文的“助體”是由呂琳琳和他的妻子葉東菊一同承擔的,呂琳琳還保留了此前“助體”角色的被動、客體化、神秘化的特點,而葉東菊則高度地寫實化了。就像她的名字“東菊”(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所隱喻的,葉東菊是作為人性(女性)最質樸自然的一種生命樣態來呈現的。盡管名字是隱喻性的,但對葉東菊生活的呈現卻是寫實的,因此,葉東菊比田林、趙慧文、田雪等任何一個“助體”形象都更有真切感和立體感。正是在與自然、真切的葉冬菊的對視和交往中,錢文認識到了自己的愛激動、愛分析、愛、虛妄和不篤定的一面,錢文作為一個歷史主體的主體化過程是與葉東菊代表的自然質樸的女性主體對話和相互詢喚的結果。
在“季節系列”中,王蒙還塑造了洪無窮和陸月蘭等“下一代”的形象,“他們”同樣與錢文的主體性成長構成了不可分割的“間性”關系。這樣,王蒙要為“一代人”樹碑立傳的的心愿實際上是通過“三代人”的詢喚與對話完成的。“一世三代”的對話結構顯然將“一代人”的傳記形象立體化、心靈化了,所謂王蒙自傳形象的“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正是體現在“代際”之間的對話中,通過不同主體之間的對話而勾勒出了當代中國“人們內心的真實情況”⑯,從而使他的“自傳性小說”具有了當代心靈史和思想史的價值和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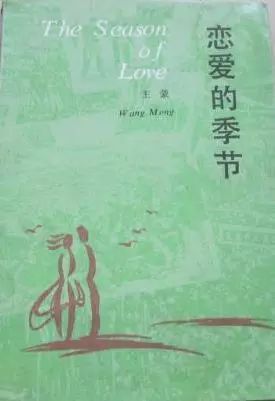
本文的寫作立足于這樣一個前提,即將王蒙“自傳性小說”中的自傳性形象視作與作家王蒙對位的一個歷史主體,從文史互證的角度這一歷史主體的歷史行狀和心靈史脈絡。從一般文藝學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立論和論證邏輯未必十分嚴謹。好在王蒙并非一個“一般”作家,他豐富而獨特的個人經歷、他強烈的意識和主體意識、他從剖析入手進入歷史的詩學方式,的確構筑了一個豐滿的歷史、現實和文學想象難分難解的“互文”世界,從文史互證角度開展的闡釋又是合理的、有效的。上文的分析至少讓我們看到了王蒙創作里別人無法替代而又鮮有論及的兩個方面:第一,作為新主義的“亞主體”“青年近衛軍”在當代歷史中的歷史際遇與心靈史。這是“歷史小說”和“新歷史小說”都少有觸及的歷史與思想史的領域。第二,作為一個中員和抒情詩人的雙重身份、總是比別人“多出一厘米”的“跨界”視野,通過將自己代入歷史,通過“代際”和不同主體之間對話化,提供了進入歷史、思考歷史的新模板:傳記與分析學相互滲透的詩學方式,提供了不失宏大和正史意味又具有心靈和思想史深度的小說新美學。
①③⑨⑬王蒙《王蒙自傳•大塊文章》,第83頁,第138頁,第175頁,第79頁,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下同。
②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四卷,第52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⑤ 菲力普•勒熱訥在《自傳契約》中將自傳的核心定義為“強調他的個人生活,尤其是他的個性的歷史”參見[法]勒熱納《自傳契約》楊國政譯,第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
⑥ 王蒙表示在1948年地下黨給他定位的是“進步關系”不是,也不是黨的外圍,當時尚沒有的青年組織,但相對于已經人黨并親歷如火如荼的活動的人而言,他又的確是一個“外圍”,參考《王蒙自傳•半生多事》第60—61頁的敘述。
⑦ “少共”(“少年布爾什維克”的提法廣為人知,但“少共”指出的主要是其身份及其特質,而“青年近衛軍”則重點他作為一個歷史主體的“代際”性質,這其中當然有“少”即年輕的意思,但更多的強調的是“近”,或者說是“距離”,是他作為“次生代”與中國新主義的歷史主體之間的跟隨、對話關系。
⑧ 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第5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
⑭金把現代小說在本質上看作是“雜語”的處所,是不同的“語言”之間的“對話”。因此,在他看來小說的根本任務是塑造“語言形象”而不是“人自身的形象”。或者說,小說塑造的沒有表達特殊語言意識的人物形象是沒有多少價值的。可參見孫先科《金的“語言形象”概念與小說闡釋的新范式》,《文藝理論研究》2005年第4期。
⑮參見[法]勒內•基拉爾《浪漫的謊言與小說的真實》中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相關論述,羅艽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