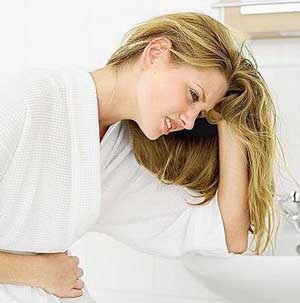男人性愛后拒絕擁抱:唯恐因過于親密迷失自己
男人為了性而情,女人為了情而性;
男人沒有身體,女人沒有靈魂;
女人是關系的動物,男人是自由的動物;
女人是情感的動物,男人是事業的動物;
……
這些流傳很廣的說法,到底成立嗎?如果成立,它們的背后又有著什么樣的奧秘?
愛情是最重要的,愛情坍塌了,自己就活不下去了。
無數女人如此感慨。
更具體地說,就是有一個男人是最重要的,他不在乎自己了,自己就活不下去了。
然而,對于女人來說,愛情是什么?
女人草莓蛋糕的愛情夢想
在《挪威的森林》中,村上春樹描述了女主人公綠子的愛情夢想。
“我追求的是一種單純的真情,一種完美的真情。比方說,現在我跟你說我想吃草莓蛋糕,你就丟下一切,跑去為我買!然后喘著氣回來對我說:‘阿綠!你看!草莓蛋糕!’放到我面前。但是我會說:‘哼!我現在不想吃啦!’然后就把蛋糕從窗子丟出去。我要的愛情是這樣的。”
綠子的草莓蛋糕的夢想,讓男主人公渡邊感到錯愕,最初讀小說時,我也覺得莫名其妙,覺得女人真是奇怪,難道這就是愛了,并且還覺得有些無聊,認為這樣的小事都被賦予了那么大的意義,真是太沉重了,怎么能準確猜透女人的心思呢,再說,猜透了又如何呢?
男人的故事又如何?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被譽為“現代小說之父”,他與女友菲麗斯訂婚,毀約,再訂婚,再毀約,第三次想訂婚時,死去了。
為什么這樣做?因為卡夫卡認為,女人是通過男人而證明自己的存在,一旦結婚,他就有法律義務滿足菲麗斯的這一需要。但是,這樣一來,他就無法投入寫小說了,而他又覺得自己是為寫小說而生的,所以他對婚姻有恐懼。
真的為寫小說而生的話,那就專心寫小說吧。但他知道,自己同時又懼怕孤獨,離不開女人的陪伴,他不要太深的愛情,陪伴就可以了。所以他選擇了和菲麗斯訂婚。她吸引力不夠,這不重要,只要有一個女人陪伴就可以了。但真到一起了,他發現,這仍然是一個沉重的義務,他懼怕,所以又毀約。
若卡夫卡碰到綠子會如何?綠子活潑可愛,心地單純,又美貌誘人,但卡夫卡會懼怕她草莓蛋糕的愛情夢想。依照綠子的說法,似乎她只要證明一次這個男人可以無怨無悔地滿足她的任性,然后就可以死心塌地地愛這個男人了。
然而,卡夫卡會知道,這種愿望會貫穿在生活中的許許多多的細節中,似乎每一個細節都要么“通過男人證明自己的存在”,要么就會覺得愛情沒有了,世界坍塌了,那實在會很沉重。
痛苦的愛情來電如同雷擊
朋友K有卡夫卡那樣的才情,也是無比敏感,而他的愛情也相當奇特。
他大一時和一個同鄉女孩相識,剛一見面,他覺得如遭雷擊,一下子被打蒙了,但這不是通常愛情的那種來電,而是非常痛苦的感受,那感受就好像在說,怎么可以有這樣的女孩,她生活在一個無比狹小的世界里,好像小到一個玻璃球那么大,但她卻全然地滿足,完全沒有意愿去看外面一個廣闊的世界。
相反,那女孩一見到他便來電了,是很美好的那種來電。從此以后,女孩開始對他窮追不舍,非常密集地頻頻到他的學校找他。
K懼怕那種如遭雷擊的感覺,所以總是逃避她。這樣過了半年后,那女孩絕望了,她打電話向他哭訴說,我到底哪里不好,你為什么不接受我……
聽到她這樣說,K心軟了,答應了她的愛,但答應的一刻,卻失魂落魄了。
更特殊的是他們第一次擁抱,女友緊緊地抱住他時,他覺得好像有一個碗口粗的木樁一下子戳到他的心里,那種感覺非常難受。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一旦確立了戀愛關系,K對女友極其在乎,總是懼怕她拋棄自己。
為什么K會有這樣的愛情?愛情不是甜蜜的嗎,他的愛情似乎一開始就是痛苦的。
我們內心的創傷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被拋棄的創傷,一類是被吞沒的創傷。小時候,若一個孩子和父母——尤其是媽媽的關系很疏離甚至經常分離,就會產生被拋棄的創傷。相反,假若父母和一個孩子的關系過于親密且父母又將孩子視為生命中的唯一的話,這個孩子就會有被吞沒的創傷。
因為有被拋棄的創傷,一個人就會無比渴望愛情,并在愛情中時時刻刻都渴望親密,這樣的人在愛情中會不明白什么是個人空間。
相反,因為有被吞沒的創傷,一個人在愛情中反而會特別留意自己是否有空間,他會隨時為自己保留一片天地,有時是獨處,有時是保守一些秘密,有時則是將注意力從愛情中轉移到別處去,甚至是背叛。
對K而言,這兩種創傷他都有,先是幼小的時候媽媽忙于工作,根本沒時間陪他,3歲前的記憶總是孤獨,他總是一個人在家中,有時有奶奶在,奶奶人很好,但很冷漠,好像根本沒有心。因而,他有了嚴重的被拋棄的創傷。
接著,等他大一些后,媽媽對他非常依賴,他明顯感覺到,對媽媽而言,似乎爸爸和其他所有親人一點都不重要,他才是唯一,他才是媽媽的百分百,但這讓K有被吞沒的感覺。
因為被拋棄,所以懼怕孤獨,因為被吞沒,所以懼怕親密,這雙重的需要和這雙重的恐懼交織在一起,令K無法動彈,他既不能全然投入到關系,也不能保持一份獨立而專心做事,就像卡夫卡一樣,既不能結婚,又不能沒有女人的陪伴。
為逃離媽媽而征服世界
卡夫卡有一個嚴厲的父親和一個非常依戀他的母親,這導致了他人生的困局。不過,對這一點,他自己似乎了解并不足夠,盡管他是弗洛伊德的老鄉,又和弗洛伊德同時代人,但弗洛伊德的理論看來沒有影響到他,否則也許他會明白,他與菲麗斯關系的困局,不過是他與媽媽關系的再一次重演而已。
卡夫卡和K都是感受力極高的男子,他們被困在了這個謎局中,但行動力極高的人一樣也會被困住,甚至,他們的行動力都可能源自于這個謎局。
亞歷山大大帝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征服者之一,他率領數萬馬其頓士兵征服了從希臘到印度的廣袤疆土。
他為什么要去征服,他的動力何在?在電影《亞歷山大大帝》中,你可以看到,他去征服的一個巨大動力,是遠離他的媽媽奧林匹亞斯王后。
與K一樣,亞歷山大大帝的媽媽將兒子視為唯一,她討厭自己的丈夫馬其頓老國王,甚至對兒子說,他不是你的父親,你的父親是太陽神阿波羅。這種討厭,在電影中似乎原因是丈夫好色成性。丈夫不再是情感上的伴侶,于是女人就容易將自己的兒子變成自己情感上的伴侶。
電影著力描繪了亞歷山大與媽媽關系的曖昧之處,很多時候,他們表現得更像是一對戀人,而不是一對母子。
這種曖昧會給兒子造成很多困惑,一方面,這是他想要的,他渴望與媽媽親近,渴望媽媽會在乎自己多于在乎父親。另一方面,這又會讓他對父親內疚,甚至還會恐懼父親會懲罰他。
不僅如此,當媽媽和兒子的關系過于緊密時,兒子就感覺自己被吞噬了,有窒息感,就要和這種窒息感對抗。
K徹底淹沒在這種窒息感中,所以他有了那樣的愛情,所以他的世界極其狹小,他是絕對的宅男,除了媽媽、妻子之外,他似乎什么都沒有。
相反,亞歷山大成功地找到了和這種窒息感對抗的辦法,那就是去征服遙遠的地方。他征服得越是遙遠,他的母后就越抓狂。在電影中,當奧林匹亞斯王后在王宮里讀到兒子的來信時,她會大聲斥責兒子。看起來,她有種種斥責的原因,但她真正想斥責的是,你為什么遠離我!但是,她不能理直氣壯地這樣指責兒子,畢竟,作為一個國王,有誰比亞歷山大做得更好?!
同時,亞歷山大也很心安,他做了一個國王最應該做的事情,但同時,他似乎又可以不必內疚。
內疚是有嚴重被吞沒創傷的人的共同情感。K說,他可以孤身一人去遙遠的金礦去做工人,他可以承受那些苦,可以專心地去采金礦,那種投入做事的感覺很好。但他又覺得自己不能這樣做,自己怎么可以背叛媽媽呢,怎么可以逃離妻子呢!
那該怎么辦呢,他想到了一個完美的解決辦法——靈魂出竅。更準確的說法是擁有身外身,一個靈魂和一個身體一起去金礦,而一個靈魂和一個身體留在家里陪媽媽和妻子。
男人為什么拒絕性愛后的擁抱
有過被吞沒創傷的人總想逃離,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男人與女人的眾多不同之處。
譬如在性愛中,很多女人并不享受性愛本身,但絕大多數女人都特別享受性愛前后的那種溫存,最好有充足的前戲,而性愛后再好好抱一會兒。但偏偏很多男人,既不愿意有前戲,也不愿意性愛后的擁抱。尤其是性愛后的擁抱,很多男人感覺上會非常抵觸。
性愛后不擁抱會讓女人很受傷,她們會想,這個男人是不是把我當作性工具,根本沒有情感。但在男人看來,他們內心隱秘的一個聲音是,如果是完全的親密,自己就會被吞沒,自己就會消失。
我的一個來訪者即是如此,他每次和妻子做愛后,都不愿意擁抱,要么是坐一會兒,要么是站起來走走,反正就是不愿意繼續親密地抱在一起。對此,他解釋說:“我不敢和妻子太親密,那樣一來好像就得背負一個重擔。”
但當我讓他多談談重擔時,他第一個想到的重擔是媽媽,與K一樣,他也覺得媽媽把他當成了唯一,而與亞歷山大一樣,他的媽媽也是不斷在他面前詆毀他的爸爸。
男人主要遭受的是被吞沒的創傷,而女人主要遭受的是被拋棄的創傷。因為怕被吞沒,所以男人要逃離親密,因為怕被拋棄,所以女人要追求親密。
逃離親密的男人總有一個安慰他的對象,亞歷山大的是征服世界,卡夫卡的是寫小說,而多數男人很容易迷上一個事物,很容易有一個愛好,逃離親密至少是一個重要原因。
最糟糕的是,男人逃到另外一個女人那里。在我參加的弗蘇摩迪的“愛的關系”工作坊中,三角戀成了一個主題,許多學員都陷在三角戀謎局中,其中還有好多學員是夫妻兩人一起來上課,想處理好這個謎局的。結果發現,追逐夢想和自由(其實是逃離親密),是有婚外戀的男人的一個普遍聲音。
譬如一個學員說:“我最多愿拿出50%的心給太太,此外我有很多夢想,為了實現我的夢想,我甚至會撒謊騙老婆,就是為了得到自己的夢想和空間。”
他還說:“我小時候媽媽比較孤獨,特別是我很小的時候,我幾歲時,常常一覺醒來發現被媽媽緊緊抱著哭。”
他婚后有兩次婚外情,但他說,準確來說叫“婚外性”,他只是在尋找刺激而已,這樣做了后,“第一是內疚,第二是委屈,因為結婚后覺得失去了自我,大概半年吧,完全和她在一起,我很痛苦,因為我看不到太陽。”
重男輕女催生包二奶現象
越是重男輕女的地區,包二奶的現象就越是嚴重,而之所以會如此,核心原因是依賴與反依賴的雙重奏。
先是因為重男輕女,所以一個媽媽在還是一個小女孩時就遭受了嚴重的被拋棄創傷。
接著,這個女人嫁到了一個重男輕女的大家庭,再一次遭受嚴重的被拋棄的創傷。在這個家庭中,她是地位最輕的一個,而且丈夫根本不是情感伴侶,因丈夫的心首先在父母那里,接著在孩子那里,接著在家人和朋友那里,她是最末一位。
沒有伴侶會非常孤獨,所以她幾乎必然要把孩子當做伴侶,如果是男孩那就會更容易。這樣男孩就有了被吞沒的創傷。媽媽被拋棄的創傷有多么重,他被吞沒的創傷就有多重。
最后,他長大了,從法律上要屬于另外一個女人了,而這幾乎要了媽媽的命,其痛苦程度就像一個妻子覺得最愛的丈夫要離開的程度一樣。于是,媽媽要和媳婦爭奪同一個男人。
在這種局面中,這個男人會非常痛苦,他覺得自己的心被分成了幾瓣,甚至自己也最好變成幾個身外身,就像K那樣。
從道德上,他屬于媽媽,越是重男輕女的地區,就越是鼓勵孝順,以至于兒子對媽媽的孝順是絕對不容置疑的頭號道德,絕對不可違背。
從法律上,他屬于妻子。現在,就算在最重男輕女的地區,也一樣受到現代文明的熏陶,明白愛情是第一位的,所以這些地區的妻子會比以前更加理直氣壯地要求愛的證明,而她們的確在法律上是有這一資格的。
但他的情感何去何從呢?當然,他對媽媽有情感,對妻子也有情感,并且就我所了解的多數個案中,其實情感還是更偏向妻子一邊,但道德壓力實在太沉重了,他在意識和行為上更偏向媽媽一邊。
那種戀愛的感覺呢?那種愛情中迷人的東西呢?尤其是輕松的兩性相悅呢?這絕不可能在母子關系中尋找,似乎也很難在夫妻關系中尋找。結果,這種需要就轉向了婚外情、婚外性或包二奶這樣的行為上。
很多男性都渴望同時擁有多個女人,但這種渴望,其實是為了逃避內疚。
有過嚴重被吞沒創傷的男性,他們看起來很想逃離親密。然而,假若真這樣做了,他們又會極其內疚。像K那種程度的,甚至僅僅因為自己有逃離媽媽的想法,就會產生巨大的內疚。所以,逃離媽媽或妻子這樣的想法,想一想就可以了,真要做的話,那不可能。尤其是,逃離妻子的想法多少還可以有,而逃離媽媽的想法,那甚至都不能意識到。
所以,絕對不可以離婚。但是,想追求輕松愉悅的兩性關系的愿望怎么辦?
最好的辦法是兩全其美,一邊保持原來這個家,另一邊再建一個家,這個家代表了道德、法律、責任、義務、忠誠和生活,而那邊那個家代表了其他一些夢想。
學會拒絕,才能學會親密
作為女性,理解男性的被吞沒創傷很重要,那樣就會明白,他們的很多行為并不是刻意要傷害你,并不是不愛你,而是他們固有的。
作為男性,深入認識你自己的內心,尤其是深入認識你與媽媽的關系,是極為重要的。
兒子與媽媽的關系,一定是雙重的,既希望親密并享受親密,又希望獨立并享受獨立。當你發現你與媽媽的關系似乎只有親密而缺乏獨立時,那一定是因為獨立的動力被壓抑了。
如果一個媽媽太渴望與兒子親密,那么這個兒子先是享受,接著是感覺到被吞沒,于是想逃離,但因此這個想逃離的愿望,又會產生內疚,覺得對不住媽媽的愛。
比內疚更深一層的,是恐懼,是害怕被媽媽懲罰,害怕被媽媽拋棄。
認識這些內疚和恐懼是極為關鍵的,因為只有化解掉內疚和恐懼的障礙,一個男人才可以真正做到允許自己追求獨立。
一個非常微妙的現象是,一些男人會允許自己的配偶犯錯,甚至是出軌,那樣以后,他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在有些時候拒絕妻子向男人要求證明自己存在的需要了。當然,這又會帶給他們更大的痛苦與糾結。
在認識內疚和恐懼的同時,可以試著從行為入手。對于有被吞沒創傷的人而言,無論男人還是女人,他們必須要學習的功課是,對有被拋棄創傷的人表達拒絕,因為每個人都是要通過自己而證明自己的存在。
在“愛的關系”工作坊中,弗蘇摩迪教大家做了三個行為上的練習:
1.穩穩地站在地上,一只腳向前,伸出一只手,對向自己提要求的人說“不!”
2.穩穩地站在地上,向前伸出雙手,對走近自己的人說“停!”
3.穩穩地站在地上,向兩邊撐開雙手,說“我要我的空間!”
這些練習,都是為了讓有被吞沒創傷的人學會直接拒絕有被拋棄創傷的人的要求。
在我的親密關系中,我是典型的反依賴者,2007年時,我對自己的內疚與恐懼有了非常深的理解,而最近半年,我在和女友的關系中,真的學會了直接說不,這對我真是很重要的一步,但也得看到,對我而言如此重要的動力,我一直到36歲才做到了基本尊重,而且我還是學心理學的,也是用于剖析自己的。
但不管怎樣,這真的開始做到了,這真的很好。